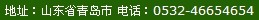|
借钱 一 夜深了,好像累了一天的人们睡得很沉。立了秋的夜晚,天气变得凉爽起来。微风吹拂着树叶,伴随清水河的流水哗哗作响。空气中弥漫着浓浓的青草和庄稼混合的味道,沁人心脾,使人不禁联想到将要丰收的希望。疯狂的杂草里潜伏着的各种小昆虫叽叽喳喳地欢叫着,与远处传来的几声狗叫彰显着这秋夜的宁静。 一所低矮的房子里仍然透着微弱的光。 陈儒江就是这个房子的主人,确切地说,陈儒江的媳妇王家秀才是这个房子真正的主人。说是房子,其实不过是三间矮房,房顶还是麦秸草的那种,也算有年头了。陈儒江本来不姓陈,也不是陈家庄人,他本姓李,五岁那年陈儒江和他一岁的弟弟陈儒海从李家庄来。来的原因是他们的舅舅、舅母膝下无儿无女,两人是过继过来给舅舅、舅母养老的。不过说起他们改姓倒也不亏,因为他们的亲娘就姓陈,就算是跟了娘姓。不过,这个说法在当时来说也算时髦了。陈儒江他爹,就是他舅陈旺财,在文化大革命那场运动中造了反,做了革命闯将。虽说当年靠着贫农的良好出身和对革命的无限忠诚打倒了一些所谓牛鬼蛇神,颇为风光了一阵儿,但运动结束后陈旺财却是学里不成,庄户不能,地里的营生干不了,庄稼荒废,生活一直很拮据。而且为了生活,陈旺财还经常做一些偷鸡摸狗的勾当,在村里的口碑不是很好,人人敬而远之。对于陈旺财的所作所为,他的媳妇既做不了主,又束手无策,只能整天唉声叹气。所以,他们至死也没有给陈儒江、陈儒海兄弟俩留下什么财产,倒是给陈儒江留下七百元的“饥荒”。那是给陈儒海盖房子娶媳妇欠下的,只不过陈儒江因为是老大才占了个便宜。这也是农村的惯例,弟弟盖房娶媳妇的“饥荒”一般由父母还,还不上或是困难就让老大分担。如果兄弟多,可以按照老二、老三的次序共同分担。反正是排行越小越轻松,这一点很符合齐鲁文化,儒家道德。 陈儒江是年有他儿子陈瑞喜那年与陈儒海分的家。说是分家,只不过分到三间破房和两副碗筷而已。用家徒四壁形容当时的境况一点不过分。分家后陈儒江的生活一直不宽裕,常常是青黄不接,捉襟见肘,好在王家秀她娘家经常接济。陈儒江不像他爹,他好学,通过自己的努力当了一名民办教师。如今,陈儒江已经转正成了正式的教师。据说他当年为了转正拼命地学习,夜以继日,居然把眼睛熬出血。当时可是吓坏了王家秀,夜里用自行车带着陈儒江回到娘家,找她做赤脚医生的老父亲。还好,只是由于过度疲劳导致眼睛毛细血管破裂,并无大碍。陈儒江也算是个地地道道的文化人,这也给他在陈家庄街面上挣回了一些面子。陈儒江生性善良、仁义、做事有分寸,但不善言谈,除了给学生讲课又表现的有些木讷,当然也可以说是老实或者说是大智若愚。也许,他媳妇王家秀就是看中了他这一点才不顾父母的反对,毅然嫁给了这个十里八乡穷得出名的教书匠。 “人家体育局的张老师和瑞喜他班主任今天又来咱家了,又问瑞喜到市体校上学的事我们考虑的咋样了。”王家秀首先打破了沉默。 陈儒江翘着二郎腿坐在炕前的杌子上,他抬起右手把廉价的烟卷放进嘴里用力地抽了一口,白色的烟雾从鼻子里涌了出来,向四周迅速地散开了。陈儒江昂着头无聊地盯着用报纸裱糊的天棚。也许白天干活有点累了,他略显得有些疲惫。 “其实,这是个好事,瑞喜体育上有天分,能有机会到城里上体校那是他的造化,要比窝在这个小村子里强啊,就是学费愁人,唉!”陈儒江低声说着连他自己都不知道能不能听见的话。他猛地又吸了一口烟,然后把烟头扔到地上,用脚尖狠狠地踩了一下,似乎有种异样的仇恨。 “儒江,要不咱们出去借借吧。不过,这年头各人的日子都不好过,跟谁也不好意思张嘴。如今又快秋收了,正是秋黄不接的时候,谁家不得添置点家什、买点化肥什么的,我估摸着也没有什么宽裕的。” 王家秀无奈地叹了口气,给熟睡中的陈瑞喜盖了盖被子,眼睛慈祥地盯着他,心里充满了歉疚。嫁给陈儒江这些年,陈儒江一直在王家庄中学教学,地里的活也帮不上什么忙,自己起早贪黑地干,生活也不见得有什么起色,眼瞅着又碰上这么个棘手的事,这样的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不过王家秀是个坚强和智慧的女人,抱怨归抱怨,那是她自己的事,她从来没有因为农活连累自己的男人干自己的事业。他觉得她的男人就不应该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下地干粗活,她固执地认为自己的男人总有出人头地的一天,她也坚信自己的日子能过好。 她如数家珍般地在脑海里想着她娘家的人,细了不能再细,生怕落下谁。但结果是让她失望的。她上有一个姐姐叫王家俊,下有一个弟弟叫王家杰。王家俊比她大五岁,嫁给了朱家庄的一个当兵的叫做朱卫国的。朱卫国虽说复员后在村里当队长,生活上是比较宽裕,但他兄妹八个,自己又是老大,下面还有三个妹妹、四个弟弟。有两个弟弟眼瞅着就要结婚了,他爹娘身体又不好,也怪愁人。说起来,姐姐对自己也算是仁至义尽了,时不时给她送十斤八斤米面接济一下,最起码瑞喜饿不着。弟弟王家杰也已经是二十几岁了,农活干不了,一直梦想着到城里当工人,去年家里托人给他在城里的粮管所找了份工作也算是成了工人,今年又在城里买了房子,已经是债台高筑了。说来也很无奈,今年王家杰四处借钱的时候,压根就没有向自己开过口。他非常知道他这个姐姐跟姐夫的能力,不说也罢。 “要不,我明天到我姐家看看吧。” 陈儒江用右手托了托足以代表自己学问的厚厚的高度黑边眼镜,又顺手挑了挑煤油灯的灯芯。往日他们并不舍得亮这么长时间的灯,他们总是在天黑之前吃晚饭,晚上陈儒江备完课就熄灯。今天不熄灯的原因是怕自己的叹息声征服不了漫漫长夜,似乎看见豆大的光亮就能捕捉到希望。 “还是算了吧,你姐的情况你又不是不知道。”陈儒江终于开了口:“明天我到老大、老二那里看看。”听了陈儒江的话,王家秀吃了一惊。陈儒江说的老大、老二就是李家庄的他的两个亲哥哥。老大是村里的信贷员,老二是村里的书记,生活上都还算殷实,要帮倒是都能帮上忙,不过陈儒江太穷了,老大、老二并不待见这个亲弟弟,包括陈儒海。以前,陈儒江他亲爹亲娘活着的时候,逢年过节陈儒江还去看看二老,每次去爹娘也多少接济一点,但每次两个哥哥却觉得自己吃了多大亏似的,对陈儒江横挑鼻子竖挑眼。而陈儒江也很清高,虽然穷,但也看不上他的两个哥哥,更看不上两个嫂子。后来,爹娘都死了,陈儒江跟他的两个哥哥也基本上断了来往,只是每年过年的时候去象征性地走一走。在家里,陈儒江也基本不提他的这两个哥哥。今天,陈儒江的决定也算是无奈之举了,尤其作为一个男人。他但凡有一点办法也不会往他们身上想。 “合适吗?” “不合适能咋地?这不为了瑞喜嘛!再说,现在正好是暑假,离入学还有段时间,正好操持操持。”陈儒江有点焦躁,他又抽出一支烟抽了起来,“你不要担心了,时间不早了,快睡吧。” 陈儒江吹灭了煤油灯,黑暗中,他看着夹在拇指和中指间燃烧得红彤彤的烟头,思绪很乱,也没有个头绪。抽完了烟,他摸索着上了炕,心想:“罢了,不去想了,想也没有用,不如睡觉实惠。”于是,他闭上眼,什么也不想,努力使自己的内心静下来。但他似乎来了精神,两眼放光,一点睡意也没有,躺在那里辗转反侧。也不知过了多久,总算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二 天亮了,太阳升了起来,又是一个晴朗的天气。院子里的老梧桐树上已经聚集了很多小鸟,它们有的在欢快地歌唱,有的在树叶间穿梭飞翔,无忧无虑,看起来要比人和谐多了。圈里的鸡咕咕地叫着,用爪子刨着地面的松土,寻觅食物。院子里几株海棠花上挂满了露珠,有的随风调皮地滴落,叶子也精神了不少。墙角的绿苔使劲地绿着,偶尔感觉有点江南的小情调。 陈儒江站在院子里伸了伸腰,随便活动了几下,又随手洗了一把脸,然后走到镜子前梳了梳头。那镜子上有一朵梅花,旁边写着“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那是去年教师节镇里的副镇长亲自发给他的,他是全镇的优秀教师。每当站在这面镜子前,陈儒江总是挺直腰板,因为那是他的荣耀,也只有在这里,他才感到轻松,自己也显得高大。他兢兢业业地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也已经有十六个年头了,他喜欢自己的职业,他爱他的学生跟爱自己的瑞喜一样。他觉得人应该崇高地活着,教师就是崇高的一种。 早饭是稀粥,还有点咸菜,只有瑞喜的手里拿着一块白面馒头,那是王家秀的大姐前几天送来的。陈儒江端着碗,粥在碗里荡漾着,稀的象水。望着这样的早饭,陈儒江无声地笑了,笑的有点苦涩。忽然,这种微笑凝固了,随即陈儒江笑出了声。王家秀爱怜地看着自己的男人,心想:“不会是傻了吧。”陈儒江看出了她的疑惑,说道:“秀,有了,陈儒巧不是当海员吗,他吃公家饭,以前写信说待遇不错,他家里这几年又没有啥花销,想必家里能攒几个,吃完饭我就去看看,保不准能行!”这几句话说得声音洪亮,犹如他在课堂上给学生讲课。说完,陈儒江低头喝粥,连喝粥的样子都生动了许多,好像不是在喝粥,而是在喝着希望。 街上已经有三三两两的人群开始准备上坡干活了,几个上了年纪的老头在街角上坐着马扎子聊天,长长的烟袋锅子悠闲地冒着白烟。前屋老光棍陈清来家没有院墙,或者说以前有,早就坍塌了。院子里长满了向日葵,只留一条小路,世外桃源一般,俨然一幅油画。那些圆圆的葵花正朝着太阳升起来的方向努力伸张着,贪婪地呼吸着新鲜的空气,叶子在风中舞动,沙沙作响。一只黑狗在前面的空地上无聊地走动着,左顾右盼,寻找着什么。 陈儒巧家在村南头靠街的大路边上,房子是七十年代盖的,比起陈儒江的家气派多了,虽然,陈儒江的房子根本与气派不沾边。 陈儒巧是陈儒江的同族兄弟,两人同岁,只是陈儒江比陈儒巧大了两个月。由于年龄相当,两人关系一直不错。尤其是十岁那年,陈儒江和陈儒巧在清水河边摸小虾时,陈儒巧不小心掉进了挖沙的深坑里,幸亏陈儒江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把他拉上来,救了他一命。事情虽然已经过去多年,但陈儒巧还是对陈儒江心存感激。后来,陈儒巧经人介绍去了海上当了船员,听说收入还不错。 陈儒巧家的大门开着,屋门却关闭着。 “香草在家吗?”香草是陈儒巧的媳妇。 见没有回应,陈儒江又问了一句:“香草在家吗?” 屋门开了,出来一个年轻的女人,容貌俊秀,但有些憔悴,两眼发红,一看就是刚哭过。 “是儒江哥啊,屋里坐吧。” “噢,那个,不了。” “儒江哥有事啊?” “那个,那个,我,你怎么啦,脸色这么难看?” “没什么。”香草低声说着,两行热泪禁不住地流了下来,香草急忙用手拭了,表情木讷。 “是不是想我家兄弟了,唉,他一人在外也不容易。” “呜呜……”香草忍不住了,竟然哭出声来,样子很委屈,她一边哭着一边蹲下身来把头埋进两个臂膀里。望着香草突如其来的举动,陈儒江站在那里不知所措,本能地呆呆地站着。他想,自己猜对了。陈儒江想安慰两句,可他又能说些什么呢?只是伫立在哪里,木然地看着眼前这个伤心的女人。 哭了一会儿,香草抽泣起来,她用手来回擦拭着眼泪,努力止住哭声。她知道陈儒江和她男人的关系,说:“儒江哥,儒巧那天杀的要跟我离婚,他不要我了。”说完又止不住哭出声来。听到这话,陈儒江懵了,他不相信这是真的,可他也不怀疑香草。这时香草已经进屋拿了一封皱皱巴巴的信出来。陈儒江接过信,仔细地读了一遍。没错,信上儒巧说他常年在外,照顾不了他们母子,觉得有愧于香草跟儿子,不如分开的好。陈儒江还是很吃惊,还是不愿相信那个朴实、厚道的陈儒巧能说出这样的话来。这也太混了,这些年香草一人在家照顾久病的公婆,照顾他们的孩子,没日没夜地操持着这个家,也实在是不容易。这是陈家庄人都知道的,尤其是那些老人,他们都羡慕老陈家有这样贤惠的好儿媳,说这不知是他们家几辈子修来的福分。这些也是陈儒巧知道的,并曾经为之骄傲的,咋说变就变了呢!陈儒江想着,不禁义愤填膺,两只拳头紧紧握了起来,要是陈儒巧在跟前那就惨了。 香草渐渐停止了哭泣,想起了什么似的,她抬起头来用手抹一把,说:“儒江哥,他外面一定有人了,我不怪他,真的。”顿了一下,又说:“儒江哥,你来是有什么事吧?” “噢,那个‥‥‥不,没事,我就是过来问一下儒巧他最近来信了没有,我好久没有收到他的信了。”陈儒江支吾着,努力找一个合适的理由搪塞。 “以前每个月来一封信,有半年多没来了,这封信昨天刚到,只是没有想到——唉!”香草平淡了许多,但脸上却还挂着明显的忧伤。 “香草啊,你别担心,回头我写封信教训一下这小子,让他别犯混!” “别劝了,强扭的瓜不甜。他要真想散,我就成全他。” “唉!这个混账东西!你要想开些啊,香草,没事到我家找你嫂子坐坐。我还有事,我就先走了。” 说完,陈儒江迅速走出陈儒巧的家门,至于香草在后面说了些什么,他也没有听清。 说实话,陈儒江并没有太多的时间去考虑香草的事,他自己的事还焦头烂额哪。陈儒江的心情糟透了,本来的一线希望也破灭了,人家出了这样的事咋开口啊。陈儒江飞快地低头走着,不知是心急还是失望。在街上他碰到了老光棍陈清来,陈清来正拄着拐棍往村外走。按辈分陈儒江要叫陈清来一声叔的。 “吆,儒江大侄子干啥啊,风风火火的?” 陈儒江抬头看了陈清来一眼,含糊地说道:“没,没什么。”也没有停步,继续前行。 “这小子,又在做文章,小心翻个大跟头‥‥‥”陈清来在他背后都囔着。 陈儒江回到家,王家秀已经上坡干活去了,瑞喜也不在家。陈儒江一头趴到炕上,他烦透了,他焦躁地掏出烟抽了起来。抽完了一支,他又拿起烟盒想再抽一支。可是,烟盒已经空了,他用力地攒瘪了烟盒,愤怒地抛到地上。“人不走运,喝凉水也塞牙啊!”陈儒江默默地想。 过了一会陈儒江逐渐平静下来。他来到院子里,倒背着双手,来回地踱着,他突然想起孟子的《孟子告子下》:“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他自嘲地笑了,他甚至想自己是不是有点太阿Q了。 没有别的办法了,陈儒江决定去李家庄找老大、老二。 现在就去。 三 陈儒江推出他的大金鹿自行车,出了家门,往北穿过胡同,来到屋后的清水河岸上。 在这里不得不说一下陈儒江的大金鹿自行车。那是陈儒江家里除了儿子陈瑞喜外唯一值钱的物件了,至少陈儒江是这么认为的。它是结婚时人家王家秀娘家陪送的。要说当时陪送辆自行车,十里八村也是少有的,这也让和陈儒江同龄人,尤其是男人着实羡慕了一阵子的。 在这里不得不说一下清水河。相传,清水河是元朝忽必烈率领万名民夫开凿的一条运河,它向南流入清荷湾,向北流入水荷湾,河名取两湾首字而成。清水河的两岸算是河堤,堤上有条小路随着河水蜿蜒着把两边的村庄串了起来,这其中也有陈家庄、王家庄、李家庄。 时间已经是八月底,再过半个多月就要秋收了。从堤上望去,田野里一片丰收的景象,各种庄稼如:花生、玉米还有那倔强的火红的高粱,将田地分割成整齐的块状,一直延伸到天边与蓝天白云衔接起来。堤上立着各种树木,尤以白杨为最多,有的已是参天大树。河里流水潺潺,不时有鱼儿蹦出水面。浅水处长满了芦苇,密密匝匝,随风荡漾着绿波。参差的野草犹如绿色长毯铺满了清水河的两岸,各种昆虫挣扎着做最后的跳跃。要是在平常,面对眼前的美景,陈儒江定会写出一首漂亮的小诗,可是现在他根本没有写作的心情,但这不妨碍陈儒江想一些愉快美好的事情。譬如说,去年麦收时他创作的《关于麦子》的三部曲长诗已经在全国著名刊物《诗刊》上发表了;譬如说,他今年创作的小说《改革的春风》已经被《人民文学》选用。沉浸在美好中的时间总是过得太快,不知不觉,陈儒江来到李家庄村后,再过去前面这座小石桥就进入李家庄了。陈儒江不得不从轻松中回到现实,虽然他有点舍不得。 陈儒江的大哥叫李世高,陈儒江的二哥叫李世峰。如果论年龄,陈儒江应该先去找李世高,但论家境他应该先找李世峰,因为李世峰是村支部书记,而且是两千多口人的李家庄的村支部书记。陈儒江觉得跟李世峰借钱成功的可能性比较大一些。陈儒江决定先到他二哥家里去。李世峰的家就在清水河南岸边上,李家庄的最西头。房子西边是一片果园,果树上挂满了各种各样的水果,今年风调雨顺,果木也喜获丰收。望着那伸出篱笆的一串串粉红的富士苹果,陈儒江还真有点垂涎欲滴。但他分明看到有人背着猎枪在园子周围巡视。要说果子的诱人远比不上李世峰家里的房子。李世峰家的房子是新盖的六间大瓦房,高度也是李家庄最高的。李家庄有个制砖的窑厂,有个苇箔厂,李世峰盖房子根本花不了几个材料费的。那年月盖房子人工费也不用付,只是主人家得一天管三顿饭。但李世峰家盖房子连饭也省了。李世峰家的院门很气派,门口大得能开进拖拉机,像是大队部的院子。 陈儒江的肚子有点饿了。这时,他看到各家烟筒里冒出了袅袅的炊烟。 陈儒江推着他的大金鹿走到李世峰家大门口。他在迈入大门的刹那忽然停住了,他想,进这样的大门是应该先迈左脚呢还是先迈右脚呢?他马上又摇头笑了,因为自己提出的这个不着边际的问题。 陈儒江的二嫂东芹正在厨房做饭。她是个苗条的女人,也学着城里人烫了头发。东芹坐在小板凳上拉着风箱,锅上冒着白色的蒸汽,从散发着的味道上,陈儒江断定锅里肯定蒸着柳叶子鱼,因为那是他的最爱。农村人一般舍不得买着吃,只是每年麦收才会买点,在割麦子时午饭吃,有过日子的一个柳叶子鱼能吃上一星期。 “嫂子!” 东芹吓了一跳,忙转过身来,从表情上看她除了惊吓还有些意外。 “吆,他三叔啊,什么风把你吹来了?” 东芹并不起身,仍然拉着风箱,填着柴火,并不时地弹一下套袖上的灰尘,态度不冷不热。这倒也在陈儒江意料之中。 “嫂子,二哥在家吗? “那死鬼又出去喝酒了,一天到头不在家,整天在酒里泡着!今早上就去了孙家庄孙大脑袋家,昨天孙大脑袋从窑上拉的砖,说是给他儿子盖房说媳妇,非要叫老二去喝酒,就他那点小算盘,不就为了省点砖钱吗!”东芹唠叨着,像是在埋怨,又像是在炫耀。她也不抬头,拉风箱的间隙还用套袖擦擦她的新皮鞋。陈儒江站在门口恭敬地听着,不免有些失望。 “那他什么时候回来?” “不知道,没准头,那得看他能不能喝醉,醉成什么熊样!你有事啊?”这时,东芹抬起头警惕地望了陈儒江一眼。 “噢,有点事。” “什么事?” “瑞喜被城里体校老师相中了,要让他到城里练体育。” “吆,这是要当运动员啊!” 东芹不屑地说了这么一句,陈儒江不知是挖苦还是表扬,他也管不了那么多,不过他坚信东芹知道了他的来意。 饭做好了,东芹起身摘下套袖来在身上抽打了几下。 “我看你哥一时半霎回不来”东芹边洗手边说。 这时候墙上的北斗星当当地敲了十二下,显然是十二点了。这个时候再到李世高家显然不合适了。午饭就在这里吃吧。 “我在这儿等我二哥吧。” 东芹见陈儒江没有要走的意思心中不悦,看来中午这顿饭是省不下了,她也不是心痛这顿饭,就是陈儒江空着手来,让她非常纠结,要知道平常来她家的人基本是多少拎着点什么的。 “他三叔,屋里坐吧,一会吃饭。你看你来的急,我也没法子准备。”东芹不冷不热地说道。 “唉。嫂子,都是自家人还那么客套。”陈儒江也捡好听的说,反正又不花钱。 “明强,你三叔来了!” 明强是李世峰的儿子,今年十岁。 “三叔来了,”明强倒是显得很热情,可能是陈儒江占了老师的光吧,明强对这个爹娘都不待见的三叔颇有好感。 明强拉着陈儒江的手把他让到西屋的沙发上。这沙发陈儒江还是去年教师节到镇上领奖时在公社办公室里坐过,软绵绵的很舒服。 “娘,昨天老赖送给我爹的茶叶呢?”明强说着翻动着桌子上大包小包的凌乱物件。 “你爹锁在柜子里了。” “我爹哪有带锁的柜子啊?” “你这孩子,不是在东屋吗!” “东屋没柜子啊!” “明强,别忙了,喝点开水就行。” 明强也不坚持,端了一杯白开水递到陈儒江手里,杯子是崭新的绿色茶杯,上面画着松树、仙鹤,还有个大红囍字,去年在镇长那里他也用过。 “他三叔吃饭吧,明强洗手去,看看你脏的,真是个祖宗!” 东芹端上来一盘萝卜咸菜,和两个白面馒头。 “娘,不是还有柳叶子鱼吗?” “净瞎说!快吃!他叔,吃吧,自家人别客气啊。” “你不是在锅里蒸着吗?” “这孩子,真不懂事,昨晚吃剩的小鱼让你三叔吃,也不怕你三叔笑话!” “你骗人!今天早上你不才到柳沟河集买的吗?” “吃吧,就你话多,不说没人把你当哑巴!” 东芹显然有些生气了,但又不好发作,只是狠狠地瞪了明强一眼。 东芹不自然地微笑着,她对陈儒江说:“他三叔啊,别听孩子瞎说,我今天早上一直在家绣鞋垫子,压根没有赶集,本来想去的,那死鬼把车子骑走了。” “嫂子,没事,我又不喜欢吃鱼,吃不来那腥。” “他叔给!” 东芹说着把一个馒头递到陈儒江手里,她将另一个馒头一分两半,一半给了明强,一半留给自己。说实话,陈儒江三十几岁的年纪,平常这样的馒头能吃俩,这也是这个年纪的年轻人的一般饭量。陈儒江思量了一下,还是把手中的馒头掰了两半,一半给自己,一半放在桌子上的饭笼里。 “吃咸菜,他三叔。” 东芹拿着筷子,指着盘里的稀疏的几块萝卜咸菜,让着陈儒江,但她自己并不吃。 陈儒江喝了一口白开水:“你们吃吧,大热天吃咸菜容易口渴。” “三叔,这咸菜不咸。” 陈儒江笑笑,勉强夹了一块。 吃完饭,明强出去耍了,东芹到厨房刷锅洗碗,一股浓浓的腥味又飘了过来。 陈儒江闲着无聊,他看到桌子上有一盒大前门烟,就拿出一支,抽了起来。“大前门”香烟在当时算得上是好烟,一般人是不舍得买的,当然也买不起。东芹收拾完走了进来,她突然发出剧烈的咳嗽,陈儒江意识到了什么,忙起身说:“嫂子,我出去溜达溜达,顺便去大哥家看看。” “他三叔坐会吧,我给你找茶叶。” “不用了嫂子,我找大哥有点事。” 东芹让着,留陈儒江再坐会儿,自己却退到屋外。 陈儒江把自行车留在李世峰家,走着去找李世高。 李家庄是周围比较大的庄了,在路上只能看到密密麻麻的房子,根本看不到庄头。八月的中午天气依然炎热,太阳炙烤着大地,好像使出了全身的力气。陈儒江脱下他的的确良小褂,只穿着背心,他把的确良小褂搭在肩上,用一只手拎着。胡同里的阴凉处三五一群地聚着乘凉的人们,他们唠叨着各种各样的不同的话题,有的用蒲扇给熟睡中的孩子扇着风并顺便驱赶着可恶的苍蝇、蚊子。几条瘦狗蹲在树荫下,伸着舌头,喘着粗气。 李世高的房子在村子中央,这个房子是在他们的爹娘死后在原有地基上翻盖的,不知不觉也有三年光景了。李世高家大门口右边有一颗垂柳,垂柳也有年岁了,树干有两个人合抱那么粗。纤细的柳条静静地垂着,形成很大的树荫。 陈儒江的大嫂翠平正坐在树下的凉席上乘凉,她肥胖的身子的左边睡着她第二胎的双胞胎儿子,面前放着一包瓜子和一把茶壶,并没有茶碗。翠平左手摇着扇子,右手有节奏地往嘴里送着瓜子,瓜子皮就吐在她前面的空地上,可能因为有时候力量不够,在她前方的凉席上零星散落着一些瓜子皮。最引人注目的是翠平右手食指上戴着的宽大的金戒指。全村两千多人,没有几个人有金戒指,就是有的几个,也属翠平的这个最大,最起码到目前无人能比。 “嫂子,乘凉啊?” 陈儒江明知故问。 “嗯,他三叔什么时候来的?” “来时晌天了。” “吃了吗?” “在二哥家吃过了。” “老二家的饭好吃啊?” 翠平揶揄着,但她总是笑着,不管她心里有多大的不痛快,这是她的与生俱来的良好行为,见谁都笑,什么时候都笑,就是嚎啕大哭都能看到她的笑意。街面上的婆娘背地里都叫她“蜜三刀”,这让陈儒江想到唐玄宗时期的李林浦,虽然他自己觉得这样并不妥。陈儒江知道翠平嫌他没有先到老大这里来,先到这里不是说翠平多么好客,因为她男人是他们兄弟中的老大,礼节上得有个尊卑先后。其实你真来了,她也不一定欢迎,只不过找人家后账是最好的占人情和给自己贴金的方法。 翠平不断地摇着扇子,额头上还是沁满了汗珠。 “下次到我们这里来,我们也不是管不起你饭。” “好,好,听嫂子的。怎么不见我大哥啊?” “他不在家,一早就到镇上办事去了。” “什么时候回来?” 翠平吐出口里的瓜子皮,端起茶壶喝了一口:“没准!”说着咳嗽了几下,她连忙放下茶壶,张开右手放在嘴边优雅地挡了挡。翠平的咳嗽跟东芹的咳嗽是不一样的。翠平的更有讲究,因为她戴着全李家庄最大的戒指,像这样的招牌咳嗽,她已经坚持有段时间了。全村人也习惯了,都知道李世高他老婆的有个咳嗽毛病。 “三弟,你找你大哥有事?你可是无事不登三宝殿!” “咱家瑞喜要到城里练体育了!” 陈儒江故意说了个“咱”,为的是套套近乎,虽然这不是他的风格,可知道人在矮檐下的道理,再说为了瑞喜也值当。 “吆,好事啊,你家瑞喜真能耐!以后出息了可别忘了我们!”翠平戏谑地说。 “大嫂看你说的,哪能呢,也不知道瑞喜是不是那块料。” 翠平又拿起茶壶对着嘴喝了起来,也不知道陈儒江说的她听到了没有。 “大嫂,我想找大哥商量一下瑞喜上学的事……” “找他商量?!” 翠平打断了陈儒江的话并白了他一眼,不过脸上仍然挂着笑。 “瑞喜上学跟你大哥商量个啥?” “这个,这个,城里上学学费贵。”陈儒江支吾着说道。 翠平将煽动的扇子停在半空中:“停、停、停,老三啊,这个事等你大哥回来再说吧,按说瑞喜上学是好事,可是,唉,跟你说不明白,还是等世高回来说吧。”其实,翠平猜出了陈儒江的心思,只是自己不好意思拒绝。但她也没有把口封死,这也给陈儒江一点希望。陈儒江跟翠平也没有什么话可说,他只能等到大哥回来再说。陈儒江呆了一会便走了,临走跟翠平说一会儿再来。陈儒江也没有地方可去,他来到清水河畔的树荫里,把的确良小褂放在草地上,顺手扯断一棵狗尾草叼在嘴里,把双手放在头下垫着,望着静静的树叶在风中轻轻地有节奏地抖动,也不想什么,反正呆一会他还会去努力。 陈儒江就这样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也许因为晚上没有睡好,陈儒江醒来的时候已经是傍晚了。天空起了微弱的风。陈儒江坐在那里清醒了一会,他心里嘀咕着:“该吃晚饭了,他们也该回来了吧。”他拖着慵懒的身体来到河边,洗了一把脸,河水很温暖。陈儒江顺着河堤向李家庄村西头的李世峰家走去。夕阳照在身上,背后长长的背影随着他有力的步伐走动。 东芹正坐在大门口的石凳上纳鞋垫,是鸳鸯戏水的纹样。听到脚步声,她抬起头来,也许她预感到陈儒江的到来。 “他叔回来了?” “回来了,嫂子。我哥到家了吗?” “那个死鬼,八成又喝醉了,到现在没见个人影!”东芹满脸怒容地说着,似乎很生气。 “噢。” 陈儒江有点失望,确切地说不是有点,而是非常。 “他叔你坐坐吧。” 说着,东芹用脚把旁边一个马扎子移动到陈儒江跟前。陈儒江意识到很可能李世峰真是喝醉了,要不这个时间也该回来了。他不回来,在这等也是白费功夫,还不如趁早到李世高那里看看,兴许他回来了。如果,他能给自己点钱,还能赶回家吃个热饭。 “嫂子,我不等了,我走了。” 陈儒江有些沮丧地推着车子往外走。 东芹站起来,把鞋垫子放在石凳上,她眼睛里放出掩饰不住的喜悦,夕阳照着她的脸上,像是刚刚结婚的新娘。她以少有的热情说道:“这就走啊,你再等等,吃了饭再走吧。” “不了,嫂子。” “那你住个三四天再来吧,你看看白叫你等了一天。” 东芹表情真诚地、不无惋惜地说。 陈儒江骑上车子,顺着胡同向南驶去,向着他的最后的希望逼近。他没有怨恨,只有失望,他清楚地知道自己的身份,他是来求人的,求人的事自然不如写诗那样潇洒。其实,陈儒江万万没有想到中午他到李世高家里时,东芹就骑着他的大金鹿到十里外的孙家庄孙大脑袋家把他来及他来的目的跟李世峰说了。李世峰当时就表了态不借钱给陈儒江,也就是他的弟弟。 “那你回去怎么开口?” “说你这个娘们咋烫了头还是见识短啊!”他抽了一口烟继续说“刘大脑袋想占砖的便宜,我能让他这么恣?我不走了,一会儿我到他家炕上装醉,顺便今晚再吃他狗日的一顿!” 李世峰摇晃着,打着饱嗝,满脸通红,唾沫星子疯狂飞溅着。东芹觉得自己的男人真是太有智慧了,真是个当官的好把式。她用右手食指放在李世峰的额头上温柔地敲了敲,露出狡黠的微笑,算是对自己男人的褒奖。李世峰给东芹递了个眼色,示意她赶快回去,一是怕让陈儒江觉察,二是怕耽误了自己喝酒。东芹搬着车子掉了个头,正欲往回赶。 “唉,唉‥‥‥”李世峰好像想起了什么,叫住了东芹:“你让老三住三四天再来!” “你想借给他钱?” “笨蛋!三四天说不定他的问题已经解决了!这样我们既不得罪他,又卖了他个人情。” 陈儒江来到李世高家,在门口正巧碰到李世高往家牵牛。这让他非常高兴,毕竟见着人了,陈儒江暗自庆幸自己的幸运。 “老三啊,听说瑞喜要到城里上学?” “是啊,大哥。” 说着,两个人走进院子。李世高拴好了牛,提了一桶水放到牛跟前,牛可能是口渴了,低着头旁若无人地饮起来。陈儒江也放好了车子。李世高的两个小儿子在院子里打闹着,他们已经三岁了。 “文化、文艺叫三叔!” 李世高大声嚷着,两个孩子也不管他,兀自耍着自己喜欢的事情。 “这东西,没有礼貌!” “小孩嘛。” “快进屋,我们哥俩喝一杯!” “大哥,我回家吃吧,你看瑞喜上学得使点钱。” “干嘛啊,到你大哥家吃饭不实落?走,你嫂子都准备好了!” 陈儒江不好再推辞,跟着李世高进了屋。屋里,翠平正将筷子放到炕上的小桌上,就放了两双。桌上有四个菜:一盘煮花生米,一盘凉拌黄瓜,一盘炒土豆丝,一盘炒扁豆。桌子头上还放着两瓶高粱酒,两个酒盅。翠平见陈儒江进来一边用肩上的毛巾擦着脸上的汗,一边招呼着陈儒江上炕。 “三弟啊,今晚跟你大哥好好喝两盅。” “一块吃吧,嫂子。” “不了,我跟孩子一块吃,这些小东西太闹腾。” “三弟,你不用管他们了,来,上炕。” 李世高和翠平的热情让陈儒江很感动,他有点始料未及,他甚至有点鼻子发酸。陈儒江分明看到了希望,并且马上就能抓到手里。两个人在炕上盘腿坐着,李世高打开酒壶倒满了酒。 “三弟好长时间不来了,来,干一个。” 两人碰了盅一饮而尽。 “吃、吃,自家人不必客套。” “好、好。” 中午陈儒江就没有吃饱,这么丰盛的饭菜自己决不能再空着肚子。陈儒江想着,便放松起来。李世高热情地让着陈儒江喝酒、吃菜,绝口不提钱的事。但陈儒江不能不提。 “哥,你看瑞喜上学还得从你这里使两个钱。” “三弟啊,我手头也是不宽裕啊,一家子人张口吃饭!” 李世高无奈地说,似乎感觉对不起他眼前的这个弟弟。 “你不是信贷员吗?你贷点钱给我,我秋收后还给你。” “兄弟”李世高指着地上的一个保险柜说:“那里面空了,昨天和今天都贷了出去。” 陈儒江有些失落,他又不甘心这么吃顿饭就回去,他伸出一只手拉着李世高的一只手。 “哥,你想想办法,秋收后我就还你,我不会给你难为的。” 李世高知道陈儒江有些醉意了,见他老是唠叨钱的事也就有些不耐烦,他手往上一抬,挣脱了陈儒江。 “我给你想想办法,住个三四天再说吧。” 李世高敷衍着说。 “哥,你真是哥,来我敬你!” 陈儒江见事情有眉目也来了精神,他连给自己倒了三盅酒,连着干了,也算是对李世高的感谢。陈儒江已是醉眼朦胧,但既然问题解决,他也彻底放开了。其实,李世高也已喝多,他的酒量本来就比陈儒江小得多。最后两瓶白酒一滴未剩。 陈儒江还有一些意识,他还要回家,至于他是怎样走出李世高家的他也不清楚了。他走在清水河岸上,摇摇晃晃地推着他的大金鹿。皎洁的月光把田野照得很亮,他能分辨出路来,所以,不必担心他会掉进河里。凉爽的风吹着他混沌麻木的大脑,他突然感觉来了酒劲,他想吐,他下意识地去支自行车,但是,晚了,他已经吐了出来,吐到了车把上,吐到了鞋子上,他能感觉出来有些污物还溅到了他的的确良小褂上。激烈的呕吐使他不得不松开手,任自行车倒在路旁,他的肚子里翻江倒海,难受之极。他捂着肚子,呻吟着。吐了一回儿,陈儒江感觉好多了,他想扶起车子坚持着回家,但两只脚里像是灌了铅,头木的要命,眼前也晃得厉害,他一个趔趄,连人带车跌倒了,车子压在身上。陈儒江想把车子从身上移开,他没有了一点力气,他只能放弃了,躺在地上喘着粗气。他看着黑色的夜空,天上闪烁着星星像是对着他微笑,他也笑了,傻傻地,痴痴地。田野里传来蛐蛐洪亮的叫声,清水河的流水潺潺地淌着,四周一片宁静。慢慢地,陈儒江在大自然的怀抱中发出了微弱的鼾声。陈儒江终于如愿以偿了,城里体校的汽车开到了他的家门口来接陈瑞喜上城里上学,瑞喜穿着一身新衣服,容光焕发,精神十足。周围簇拥着来道喜的乡亲们,陈儒海来了、王家俊来了、王家杰来了、老光棍陈清来来了,王家秀高兴极了,脸上笑开了花。人总是这个样子,在现实中困难的事,梦里却能如愿以偿。 四 陈儒江地当床,天当被地睡了一个晚上,他醒来的时候已经是天色微明,远处传来了此起彼伏的鸡叫声。陈儒江的衣服被露水打湿,他感觉到很深的凉意,他情不自禁地打了一个喷嚏——他感冒了。头还是有些麻木,并有些轻微的痛,口里干燥的很,渴的厉害。但有一件事陈儒江是非常清楚的,那就是昨晚他的的确确是醉了,而且在这里睡了一夜。陈儒江扶起车子,来到河边洗了一把脸,拾掇了一下头发。他的内心是高兴的,毕竟钱的事还有希望,钱的事有希望,瑞喜的前途就有希望。 回到家,天已经大亮了。陈瑞喜刚刚睡醒,正在院子里洗脸。见到陈儒江进来,他迫不及待地问:“爹,你咋才回来,昨晚在大伯家住的?” “嗯。”陈儒江无精打采地应了一声,接着打了个哈欠。 王家秀正在院子里喂鸡,她看见陈儒江的尊容,放下手中的家什,用围裙擦着手,惊诧地走过来。她拍打着陈儒江身上的土。 “他爹,你这是唱的哪一出啊?” “没事。”在田野里睡一晚上毕竟不是什么光彩的事,陈儒江只能随声附和着。 “事办得怎么样?” “大哥的钱都贷了出去,二哥可能喝醉了,到晚上也没有回来。不过他们让我过几天再去看看。” “我寻思着也不会太顺利!” “饭,”话还没有说完,陈儒江打了一个喷嚏“饭做好了吗?” “做好了,瑞喜,吃饭!” “吃完饭你给我熬点姜汤,我发一下汗,可能感冒了,鼻子也有点不透气。” “中。” 一家三口正在围着桌子吃饭,陈儒江的弟弟陈儒海走了进来。 “哥、嫂子吃饭哪?” “他叔来了,吃了吗?” “吃了。哥,快秋收了,今天我们去把场院压压吧,这事及早不及晚。” “一会让你嫂子跟你去吧,我刚从李家庄回来,有点感冒,一会儿发一下汗。” “你去李家庄干嘛?” “瑞喜被城里体校的老师看中了,想让他到他们的体校练体育。我捉摸着这是个好事,就是学费不凑手,我去借俩钱。” “咋样?” “钱没拿到,住几天再去看看。” “我看够呛!” 陈儒海比陈儒江小五岁,他头一胎是个闺女,如今他媳妇又怀孕了。陈儒海现在住的房子以及他结婚的事都是陈儒江给他操持的。他们分家时,父母,也就是他们的舅舅、舅母偏袒他,把七百元的饥荒全部分给了他哥哥陈儒江。七百元在当时不算是小数目,陈儒海觉得事情有点过分,但他说了不算,再说,他媳妇跟他结婚时说好不要饥荒的。这些让陈儒海耿耿于怀,他始终觉得自己对不起他哥跟他嫂子,但他又无能为力,他只能帮陈儒江家多干点农活来弥补心中的歉疚。论生活,陈儒海要比陈儒江好得多,但他结婚这几年也没有什么节余。如今,侄子上学也算是大事,不能不帮,可囊中羞涩又使他没了主意。陈儒海蹲在门口,拿出烟包和烟纸熟练地卷起一颗烟,用火柴点着,大口抽了起来。他望着吐出的烟圈发呆,也许他在想着如何帮帮他的侄子。 “他叔,一会儿吃完饭我就到场院去。” “嗯。哥,要不我到姜文凤家借点钱应急吧。” 陈儒海说的姜文凤是他的媳妇,姜文凤家也就是他丈人家。姜文凤的爹叫姜炳全,是个做豆腐的,人称“豆腐姜”。姜炳全就两个闺女,大的叫姜文娇,嫁给了本村一个姓宋的木匠。姜文凤是他的小闺女,嫁给了陈儒海。姜炳全平日里做豆腐,十里八乡地到处吆喝着卖,由于他的豆腐不扯豆腐皮,所以口感好,销路自然也好。姜炳全种着几亩地,但那基本都是他老婆的事。姜炳全两口子都是过日子的好手,生活宽裕也省吃俭用,自己舍不得花钱,对别人更是吝啬。他的两个闺女也潜移默化,跟他爹娘有过之而无不及。陈儒海没想着自己去跟他丈人借钱,他想动员自己的媳妇回娘家去借,陈儒海想瑞喜上学这样的大事姜文凤理应帮忙的。 “不用了,你媳妇的脾气你又不是不知道,再说她还怀着孕,别伤了和气。” 其实,那天夜里陈儒江在炕上辗转反侧的时候也想过这事,但他马上否定了,他很明白姜文凤的为人,他不想让陈儒海为难。“哥,嫂子,你们就听信吧!” 陈儒海知道陈儒江的顾虑,他说得斩钉截铁,好像是十拿九稳。他把烟头摁在地上拧灭,然后站起身来,把烟包和烟纸放在口袋里,走了出去。望着陈儒海的背影,陈儒江无奈地摇了摇头。 街上,老光棍陈清来坐在自家向日葵前安闲地抽着烟袋,看到陈儒海他搭讪道: “大侄子,这是忙啥啊?” “忙营生,谁像你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 陈儒海没好气地回答,他不是故意对陈清来不敬,毕竟他得叫他一声叔。陈儒海也是为瑞喜的事着急。 “咋了?像是谁欠了你二百吊。” 陈清来吸着他的烟袋,仍关切地问着,脸上堆满了皱纹。 “跟你说了,你也办不了。” “不说更办不了。” 陈儒海见陈清来执着,就把瑞喜要到城里练体育和缺钱的事一五一十地跟他说了。陈清来听了没有言语,只是啧啧地摇头叹了声气。 陈儒海也不跟他计较,继续往家走。 姜文凤正坐在炕上给她将出生的孩子织毛衣。 “凤,跟你商量件事。”陈儒海笑着说。 “啥事?” “瑞喜被城里的体育老师相中了,要带他到城里练体育!” 姜文凤听着,手里依然忙着自己的营生。 “看把你给乐的,像是你要去城里似的。你还别说,瑞喜这孩子还真中,你看咱哥咱嫂子都不是那块料。” 陈儒海见姜文凤心情还不错,自己也放松了许多,他甚至有点怪自己小看了姜文凤。 “是啊,保不准以后这小子有出息!这也是咱家的荣耀!不过,瑞喜上学的学费还没有着落。” 说完,陈儒海看了姜文凤一眼。 “没着落也没办法,咱又没有钱。” 陈儒海有点失望,他还没有提到借钱,姜文凤已经把路给封死了。陈儒海还有些不高兴,但又不好表现出来。 “唉,我说,瑞喜上学也是件大事,要不咱帮帮?” “你想啥哪,你哪里来的钱帮?!” “嘿嘿,咱是没有,可你爹肯定有。不中你回去借点,反正也快秋收了,秋收完了再还上。” 听到这话,姜文凤停住了手里的活,抬起头来,眼瞪着陈儒海。陈儒海从姜文凤的眼神里明显读出了一个“不”字。 “要借你去借,我不去借!” “咱又不是不还,你回去借不是方便嘛。” “他拿什么还?你别忘了,他家还有七百元的饥荒!” “那饥荒还不是为了咱!那饥荒应该咱还!”一提饥荒,陈儒海有点激动,要不是这饥荒,他哥也不会这样困难。 “你吼什么,陈儒海!这可是咱结婚时说好的,一进门就有饥荒,谁嫁给你这穷种!”听到陈儒海话里有气,姜文凤的嗓门也提高了。其实,姜文凤何尝不知道陈儒江的七百元饥荒是为了他们,但她不愿提,因为她知道自己的男人跟他哥哥感情深,她怕哪天陈儒海上了神经把那饥荒要过来,那她就累了,惨了,她从小没吃过这样的屈。 “穷种怎么啦,当初谁给你捂着眼了?!那是谁?那是我哥,那是我侄子,我不帮,谁帮?!” 陈儒海见自己的媳妇如此不通情达理,感到很失望,连着旧事重提,他彻底爆发了。他狠狠地把抽着的烟扔到地上,顺手又卷了一支。姜文凤看着眼前的男人仿佛陌生了很多,结婚以来,她还没有看到自己的男人对自己这么大动肝火,而且是为了别人。她感觉到委屈,她感觉到自己不能承受,她愤怒地把手里的毛衣扔向陈儒海。 “帮、帮、帮!你去帮吧!” 陈儒海敏捷地用手把扔过来的东西挡在地上。 “疯婆子!” 陈儒海骂了一句,摔门而去,背后传来玻璃破碎的声音和他的女人的哭泣声。 五 陈清来听说了瑞喜的事以后,仍坐在那里抽烟。他出神地看着一院子将要收获的向日葵,看着他的老屋。他已经七十多岁了,已经是风烛残年。他一生也算是坎坎坷坷,他做了一辈子老实巴交的农民。他胆子很小,早些年战争的时候,十里八乡的青年不少在红高粱地里干过鬼子,打过国民党,陈清来不敢,他听到枪声、炮声两腿就发软。陈清来一辈子没有当过兵,连个民兵也没有当过,甚至没有到前线去支前。陈清来一直在家里种地,一直到他干不动了。其实,陈清来结过婚,有过两个儿子,就在大儿子21岁,小儿子18岁那年,他送他俩去当了兵。因为,陈清来知道自己一辈子胆小,他不想让两个儿子和自己一样窝囊。不过,他没有想到的是他的两个儿子后来都去了朝鲜战场,又都牺牲在那里。陈清来的媳妇经不住痛失儿子的打击,疯了,没过几年就死了。从那以后,陈清来就再也没有续弦,独自生活了二十几年。但幸运的是他身体还算硬朗,精神也很好,见人爱说话。陈清来是个倔强的老头、可敬的老头。街面上连孩子都知道他的两个孩子都在抗美援朝的战争中牺牲了,在那样一个崇尚英雄的年代,人们对英雄的父亲自然也是尊重有加。当时国家对烈属有一定的补贴,但陈清来拒绝了,他说国家不容易,自己能自食其力。直到这一两年,他上了年纪,地里的活确实干不动了,才享受了村里的五保户待遇。陈清来生活上虽说是清贫,但温饱不成问题。 陈清来抽着他的烟袋,深沉地,在这样一个清晨里。他自己也不知过了多久,也不知填了几袋烟,他悠悠地把自己的一生过了一遍。忽然,他表情严肃起来,他做出了一个决定,一个仅次于送他儿子当兵的决定,一个在他看来一辈子不会后悔的决定。 陈儒江喝了姜汤正在炕上盖了被子捂汗,王家秀已经领着瑞喜去场院干活了。虽然是白天,屋里的光线还是很暗。从窗棂上隔着一层白纸透进来的光线照着陈儒江愁楚的脸上。他回忆着昨天到李家庄的经过,他感觉钱的事还是有希望的,毕竟是亲兄弟,毕竟这是关乎陈瑞喜一辈子的大事。正想着,门吱呀一声开了,陈清来拄着拐棍走进来。 “大侄子这是咋了?” “清来叔啊,嗨,有点感冒了,正发着汗呢。清来叔,坐吧。” 说着,陈儒江就要坐起来,陈清来急忙阻止:“别动,躺着就行!” 陈清来坐在了炕前的杌子上,两只手扶着拐棍。 “大侄子,听说瑞喜要到城里练体育?” “是啊,可是学费还没有着落,眼看就要入学了。让你见笑了,清来叔。” “看你这孩子咋说话呢,我还见笑!我也替瑞喜发急!”陈清来说着拿起拐棍在地上用力敲了两下。 “有什么办法呢?”陈儒江声音很小,像是自言自语。 陈清来把拐棍放在一边,站起身来,慢慢地从下衣口袋里掏出一个卷成卷的小手绢,把它放在左手上,然后用右手轻轻地翻开,里面露出了被同样卷成卷的钱。 “大侄子,我这里有八十元钱,原本是想给自己留个棺材板钱,但看现在这状况,一时半霎我也死不了,就先给瑞喜上学用吧。” 陈清来和蔼地说着,满脸的皱纹堆了起来。他把钱放在炕上,又把小手绢叠起来慢慢地放进口袋里。 “不,不,叔,我们不能用你的钱!” “咋了,我的钱不当钱使?”陈清来装了一锅烟抽了起来。 “叔,你不容易!”陈儒江说着,感觉眼角有点湿润。他不是不需要钱,而是陈清来的钱他不能要。他也压根没有想到陈清来会主动借钱给他,意外之余,陈儒江心里充满了感动。 “别说了,什么事也没有娃上学要紧!” “叔!” (待续) 陈圣原创作品长按北京哪家医院皮肤科治白癜风好北京看白癜风效果最好专科医院
|
当前位置: 鬼子姜_鬼子姜食品_鬼子姜挑选 >短篇小说借钱上
时间:2016-11-28来源:本站原创作者:佚名
------分隔线----------------------------
- 上一篇文章: 内调立夏之后你要吃的nbsp古法
- 下一篇文章: 萝卜与姜为什么不宜同吃